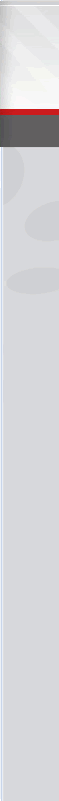讲座名称:日本文艺的审美传统与交流
主讲人:叶渭渠 (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)
讲座地点: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
讲座时间:2004年07月17日
讲座类别:艺术
讲座时长:120分钟
主讲人简介:叶渭渠 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教授。曾任早稻田大学、立命馆大学、学习院大学、横滨市立大学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、日本“野间文艺翻译奖”评委会委员等职。
学术专著有:《日本文学思潮史》、《日本文化史》、《冷艳文士川端康成》等。与唐月梅合著有:《日本文学史》、《20世纪日本文学史》、《日本人的美意识》。多人合著有:《日本文明》、《世界文明图库?樱花之国》等。另有散文随笔集:《樱园拾叶》、《扶桑掇琐》、《雪国的诱惑》。译有:加藤周一著《日本文学史序说》、川端康成《雪国》等系列小说散文。主编有:《日本文化与现代化》、《东瀛美文之旅》,以及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大江健三郎、谷崎润一郎、横光利一等名家文集十余套。
关键词:艺术 日本
组织单位:国家图书馆古籍馆(原国家图书馆分馆)
内容摘要:本题分两大部分:第一部分是古代“真实”和“物哀”审美意识的流变;第二部分是近古空寂?闲寂的源流与历史联系
第一部分是古代“真实”和“物哀”审美意识的流变
古代的“真实”审美意识是在日本本土文化思想──原始神道文化土壤中萌芽和生成的。日本古代审美学意识从萌芽到发生的全过程,都是以“真实”(まこと)为基底的。在不同历史时期,分别接受外来佛教的“心性”和禅宗的“无中万般有”的思想影响,融合在比如古代的“物哀” (もののあはれ)、近古的“空寂”(わび) 的幽玄和“闲寂”(さび) 的风雅等审美意识中,成为不易的日本美学精神,流贯于各种日本文艺乃至生活意识之中,成为日本文明的河床。
“真实”审美意识
日本古代的“真实”审美意识,除了表现“事”、“言”的真实以外,还表现“心”的真实,即“真心”、真情的一面。
在文学方面,《万叶集》所表现的“真实”审美意识,以真实的感动为根本,尤其是后期的恋歌,更多的真实的感动表现为“真心”。其表现的“真心”,主要是人对四季自然的真实、自然、素朴的感受性,以及人在爱情生活上的悲喜哀乐的自然感情。这是凡人的人性真实的一面。这就是文艺上的“真实” 原初审美意识。
紫式部创作的《源氏物语》正体现了这种写实的“真实”审美观念。它的表现内容以
真实性为中心,如实地描绘了作者所亲自接触到的宫廷生活的现实,不是凭空想写出来的。作者紫式部无论是在文学、美学的理论主张上,还是在创作的美学实践上,都确实是一位卓越的写实主义作家,《源氏物语》是日本古代有数的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优秀文学作品。
在美术方面,从原始美术到古代佛教美术,除了具有宗教的神秘性的艺术意匠的一面,还具有写实性的艺术形态的一面。在土偶、埴轮、佛画、佛雕,乃至某些初期的人物塑像,都表现了日本古代绘画、雕塑艺术所追求的写实的真实性。
综观日本古代各种文学艺术形态,都存在“真实”审美学意识,主要表现人性的真实,同时也表现美的体验,即把握人性与美两方面的真实性。这就是日本古代“真实”审美的基本性格特征。这样,“真实”的美学意义,人性是根本,真是为了美,真也是美的一个要素。这种审美精神贯穿于各个时代,成为不易的东西。这种审美意识,从不自觉,到逐步走向了自觉,从此“真实”审美意识,左右着日本古代审美的价值取向,也成为古代日本文艺的基本精神。
“物哀”审美意识
日本“真实”的美学意识与“哀”(あはれ)和“物哀”的美学意识,是先于美学的其他形态而存在。“物哀”的形成与发展,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,最早是与“真实”美学意识孪生,深深地渗透和参与古代日本美学思想的形成。
“物哀”的审美观是由紫式部之手完成的。紫式部在《源氏物语》中,以“真实”为根底,将“哀”发展为“物哀”,将简单的感叹发展到复杂的感动,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,并由理智支配其文学素材,使“物哀”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充实,含赞赏、亲爱、共鸣、同情、可怜、悲伤的广泛涵义,而且其感动的对象超出人和物,扩大为社会世态,这种感动具有观照性。紫式部将“哀”发展为更富多义的“物哀”审美思想,创造了日本式的浪漫的“物哀”审美理念,从而确立了日本古代美学的主体性。《源氏物语》一书,就出现1044个“哀”和13个“物哀”的词,尤其是她笔下的13个“物哀” ,具有多义性。
《源氏物语》的物哀之多义性,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: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,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;第二个层次是对世态的感动,贯穿在对人情世态、包括“天下大事”的咏叹上;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,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,即对自然美的动心。前两者是属于现实性的,后者是属于观照性的。但是,所有“物哀”的感动、“知物哀”心,都是从内心底里将对象作为有价值物而感到或悲哀、愤懑,或愉悦、亲爱、同情等等纯化了的真实感情,而非单纯的触物感伤或触物兴叹,更非一般动物的自然感情。为了挖掘这三个层次的“物哀”之情和“知物哀”之心,作者前所未有地着力于心理描写,挖掘人性的深层的真情,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紫式部主导的“物哀观”支配着平安时代日本古代文学,而且其影响及于这个时代以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文学美学观,甚至超出文学美学观而及艺术观、文化观和人生观。
日本古代“物语绘卷”这一美术形态中,最具代表性的《源氏物语绘卷》,不仅将各回的故事、主人公的微妙心理和人物相互间的纠葛,还有人物与自然的心灵交流,惟妙惟肖地表现在画面上,而且将《源氏物语》的“物哀”精神融入绘画之中,将《源氏物语》的神髓出色地表现出来,颇具艺术的魅力。
第二部分是近古空寂?闲寂的源流与历史联系
中世纪以后,在禅宗思想的强烈影响下,在审美意识方面,由古代以“真实”、“物哀”为主体的审美观,转向这一时期以“空寂”的幽玄、“闲寂”的风雅为主体的审美观。“空寂”和“闲寂”的美学理念渗透到日本文艺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。以“空寂”的茶道、空间艺术和“闲寂”的俳句为例重点说明。
空寂的审美意识
千利休以“空寂”作为茶道的基本精神,创造了草庵式的茶道,并进一步提出的“空寂”是以“贫困”作为根底,“贫困”则是空寂的本质构成。所谓“贫困”,是指不随世俗,诸如财富、权力、名誉等等,企图从“贫困”中感受一种超现实的存在。因此他强调“空寂茶”不能为“物”所囚,必须以“心”征服“物” 。
在空间艺术方面,最具代表性的是桂离宫的建筑。它的明显特色是:质朴而近乎自然,非对称性而近乎不完整乃至残缺,且小巧而几近纤弱。这种审美情趣不重形式而重精神,是从禅宗“多即是一,一即是多”的思维方法的启发而产生的。它表现的平淡、单纯、含蓄和空灵,让人们从这种自然的艺术性中诱发出一种空寂的效果,产生一种幽玄的美。
日本庭园艺术受禅文化精神的渗润最大的,是“枯山水”庭园,即石庭园的一种俗称,就是用石头、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,缓慢起伏的山峦,或造成山中的村落等等模样,企图让人生起一种野景的情趣。”到了室町时代,禅宗广为传播后,导入了“空寂”的“幽玄”艺术精神,才形成一种独立的庭园模式而流行起来,成为日本最具象征性的庭园文化。
这种“空寂”的幽玄美,还体现在能乐和水墨画上。世阿弥的“能乐”论著《风姿花传》,成为近古艺术理论的基础概念,使之具有独自的美学意义。他首先强调要达到“幽玄”,就必须“有心”;其次,强调“能乐”的演员表演主要动“心”才有“空寂”的“幽玄”。这是日本近古美学的一大跃进,是划时期的大事。
日本传入中国南宋的水墨画,又独创了与中国水墨画审美情趣相异的风格,即以自然为主的水墨山水图,深藏禅机的风格。雪舟不使硬笔法,而采用柔和、湿润的表现法,以适应日本人的感觉。同时,通过余白和省笔,浸在空漠的“无”中来创造一种超然物外的艺术力量,从“无”中发现最大的“有”,并由此确定其艺术美的价值,完全体现了日本的“空寂”幽玄的美学精神。
“闲寂”的审美意识
芭蕉“闲寂”的美学观,其根本源于:一是日本传统的“真实”(诚)、“物哀”、“幽玄”文学思想。芭蕉以古代传统的歌情作为媒介,捕捉自然物象的固有生命,并将此固有生命称作“本情”,以为风雅终极的目的。这是离开自我的小主观,归入自然的本情,并通过两者合一,走向大宇宙。而这种艺术观的根底就在于“真实”(诚),并且与“物哀”与“幽玄”浑然一体。二是中国老庄思想和朱子学世界观。芭蕉将老庄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和朱子的“天道即人道”思想移在俳句上,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,觅寻俳句的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。他所主张的“贯道之物一如”,就是老子主张的顺应自然,则必须“惟道是从”,抱守着本体“一”也。在表现上,则深受汉诗内在张力的表现的影响。他的“闲寂”看似是消极无力,但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。
日本美学还有许多形态,但占据着重要的中心位置的,是古代的“真实”、“物哀”和近古的“空寂”、“闲寂”,它们彼此相辅相成,形成日本美学的特质,概括地表现了日本审美观的整体。一位日本学者论述“物哀”、“空寂”、“闲寂”三者在日本审美观构成方面的重要性时说:“如果物语没有‘物哀’的形象,茶道没有‘空寂’的形象,俳句没有‘闲寂’的形象,就如同调膳忘却下佐料。它们的美形态占据着日本美的心脏部位。”这是很形象的概括,在这里,我补充一句,这三种日本美的形态,都是以日本本土的“真实”美形态为根基而形成的。可以说,日本美学是有其色彩鲜明的民族特质的。
写实的“真实”、浪漫的“物哀”、象征的“空寂”和“闲寂”这四种精神相通的美学思想,大大地增加了日本民族文艺思想的丰富性,以及艺术表现的力度,进一步深化了日本文艺美,完成了日本美学的体系。
我们通过它们可以发现日本美的存在,可以得到至真至纯的美的享受。